
台灣世新大學在今年1月2日的校務會議表決,2020年停止旗下的社會發展研究所(簡稱社發所)招生。校方指該所招生不足、休學退學率高、畢業率低,因而決定停招;反對者則認為校方不合程序,沒有跟研究所教師好好商量、㝷求停招以外的處理方法。這在筆者看來並不是要害所在。圍繞少子化、院校自主的爭辯,筆者亦認為不著邊際。兩岸三地社運界在反對社發所停招這場運動中提出的核心論點,反映的是「社運產業」在階級社會中的自我定位和根本侷限。
反對者最重要的論點,是該所多年來栽培大量社運幹部乃至議員官員的「社會價值」,地位超然,即使收生不足,也要永續存在。反停招者向校方、政府喊話的重點,就是提醒他們社運幹部們引導、平抑資本主義社會壓力,鞏固公民社會的功能,而停招將會是破壞這種機制的愚行。反對停招者找來了兩年多前曾被社運圈批判沒有認真反對蔡英文政府砍七天假的綠營「進步」立法委員做見證,說社發所啟發了她們的「批判思考」和「碰撞體制的實踐」,則直接地展示了社運界對於資本主義體制的依賴,及其「社會批判實踐」的極限。
事實上,無論是資產階級國家主辦的國立大學、還是由個別財團經營的私立大學,都不會容許主張反對、甚至推翻資本主義的學系乃至教員的存在。在冷戰結束的1990年代,在帝國主義操盤的所謂民主化(即推動取代軍事獨裁、維護帝國根本利益的有序權貴政黨輪替)的特殊政治環境之下,台灣部分大學(包括與民主完全沾不上邊的梵蒂岡系統)曾經大力栽培「非共」的社運幹部,用以抵制白色恐怖幸存者所領導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在也曾是冷戰前沿、同樣經歷過數十年殘酷的親美軍閥獨裁統治的南韓和菲律賓,都有類似的「開明資本」和梵蒂岡大力培訓「非共」社運幹部、組織「公民社會陣營」,以「民主進步」的名義同反帝左派爭奪群眾、鞏固當地新殖民體制的基層基礎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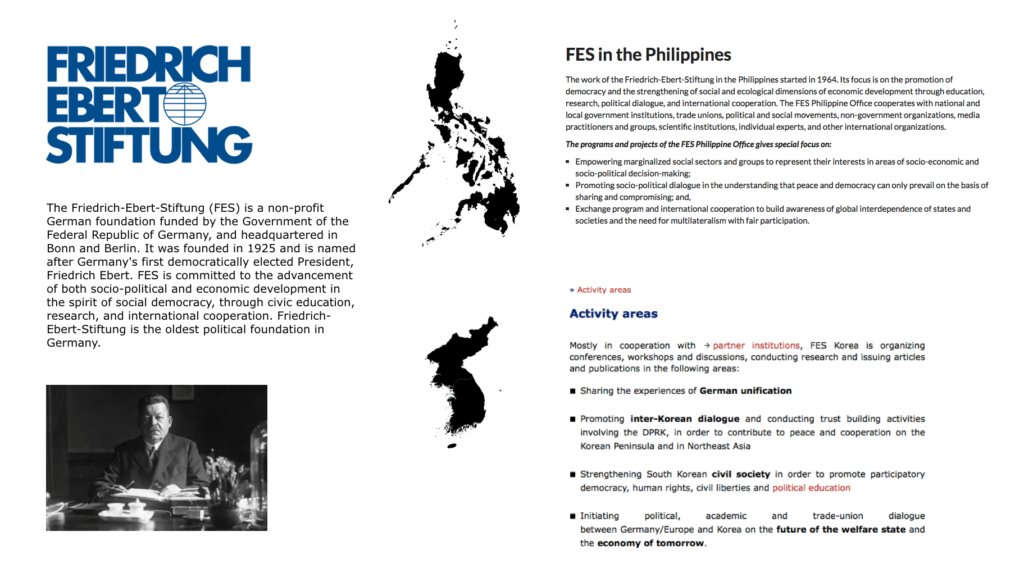
在歷史上,在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社民化之前,從來都沒有讚揚某資本家的「自由學風」、宣傳他們經營的院校是不可替代的社會研究場地的說法。革命時期的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總是自己籌集人力物力建立黨校,向工人群眾和黨員幹部傳授社會科學。他們不會宣揚資產階級學院有義務為工人運動培訓幹部的「公共性」,也拒絕任何依賴資產階級資助的思想,將組織的創收、建立獨立的經費來源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羅莎·盧森堡就曾是德國社民黨黨校最有名的教員。在她的影響之下,社民黨黨校是左派的陣地。與此同時,去黨校進修的多數工會、機關領導和國會議員,看重的是黨校為他們補充實務知識(在當年,了解資本主義的運動邏輯、而不是示威請願立法的「運動」流程,被看作是十分重要的實務)、幫助他們在德帝體制內出人頭地的作用,而貶抑黨校傳播、完善和實行革命綱領的功能。但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沒有宣揚應當依靠資產階級辦學的做法。從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的需要引申而來的工運政治獨立和自主辦學的宗旨,隨著社民黨的官僚化和全面融入資本主義體制,被抹煞和故意遺忘。
在一百年前的柏林起義之中,認定改良對他們最有利、因此「對工人運動」亦最有利,獲得了德國統治階級授權的社民黨黨校高材生集團,指揮極右派軍閥獵殺了他們曾經高度讚揚的老師盧森堡。只是在此之後,自稱社會主義者之中,才會有人宣揚工運和資本的全面合作,包括對黨和工會的宗旨和經營有決定性作用的幹部的培訓。
兩岸三地社運界對可以說是一戰後白色恐怖後遺症的「官許、商辦」社運幹部培訓模式的推崇,最終還是沒有社會主義運動、甚至是沒有人願意準備建立社會主義運動的症狀。對於善長仁翁和「自由學風」的宣揚,到最後不過是美蔣白色恐怖奠基的、再由「台灣民主」鞏固的自由主義政治正確的表現。在世界自由主義的共識瓦解,資產階級已經無意向傳統改良主義大量投資的當下,這種說法只會更加蒼白無力,進一步使現存社運走向式微,甚至杜絕主觀上追求進步的青年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