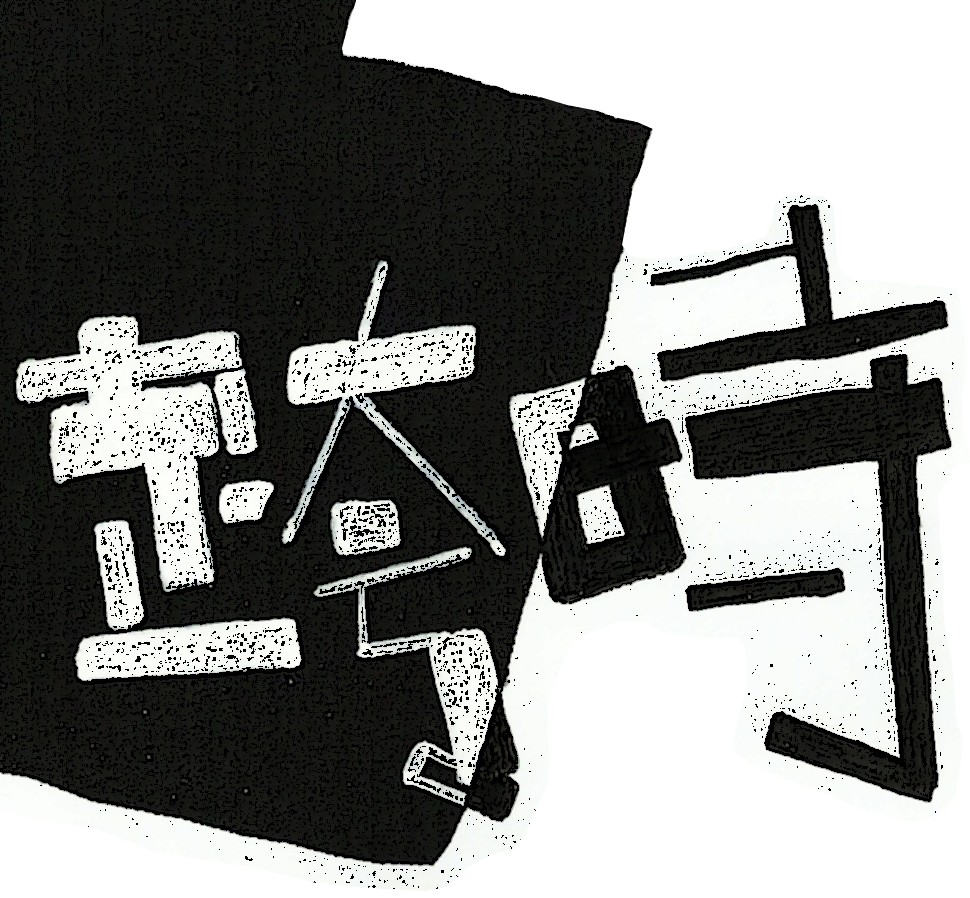文/李維怡
按:
編輯來函,要寫末日:「末日為切入點,反省當下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文化狀態。如果說二三十年前我們還在想像近未來的末日世界,那今日就是那種末日的實現。末日是一種感覺,甚至是欲望。對現實的無力感或無所希望轉換成一種歷史的終結,彷彿我們就是尼采所謂的Last Man,又或某義意上的黑暗時代……意欲探討這種末日狀態的由來,或解除這種狀態的出路……」
收到稿約時正在咳到甩肺大病中,一定是病到失心瘋才會答應這種稿約……
有無好死
不得好死。
在與死亡有關的咒詛語中,這一句堪稱歹毒和復仇性最強:不單要終結他人的存在,更要他臨死受大苦難--由於明知死沒有將來,痛苦便失去被超克的意義,但痛苦卻又是非常真實的感覺,真是絕望加痛苦的最差組合……
《第七封印》的主線,可能,從頭到尾,就是在問:「點樣得好死」?這句話包含的意思可以很廣泛,比如說:死得心安理得、死得其所、死而無憾、含笑九泉、死得安慰、死得重於泰山……
一開筆就死死死死,皆因對於一大堆末日說法,我認為無非都是怕死而已。就連柏格曼大叔自己都說,拍這齣影片是用來克服自己對死亡的恐懼。死亡不特別,怕死也很普通,只是,其實「怕死」即是怕什麼呢?為何柏格曼克服個人的怕死或壯膽之作,要以一種大量集體無意義死亡(聖戰和瘟疫),來包裹著主角和配角們最後的生與死呢?為何要讓主角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他對上帝的疑惑?又為何最後,一行人在死神的帶領下,竟在天際線上列隊跳舞呢?
藝術作品做了出來,觀眾有責任去合情合理地詮釋,雖未必與原作雷同,但不失為藝術品生命無限衍生的方式。在詮釋中,不同的框架,協助我們看到不同的東西。《第七封印》是一個意象豐富的寓言體結構,要每一個有意思的地方都談,可不得了,故根據編者的要求,便以「末日」為框架,開啟我的第七封印吧……
末日到臨 誰當覺醒?
末日與一般個體死亡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大量、集體。同時,末日也不像一般的天災後死傷慘重的情況,因為,它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球化」、世界性的終結。再也者,如果從宗教角度而言,不論是基督教的啟示錄或是古蘭經的聖訓,末日論皆與人的集體犯罪有關,例如偽神獲得廣泛的傳播和接納、道德淪亡、甚至是人類不斷興建摩天大樓等等,都可以是末日的徵兆。換句話說,末日便是神/真理對「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已忍無可忍,故發動無差別的毀滅性攻擊(在人類之間我們叫這做「恐怖主義」)。
聖戰和瘟疫就是整齣電影的基本設定,而聖爭和瘟疫,似乎都符合上述末日的條件。
電影的主角騎士安東尼奧,就是一個剛打完聖戰回歸的人,但他卻說,死前要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換句話說,十年聖戰,十年青春,於他而言竟毫無意義,全屬浪費。從歴史中我們知道,偽神論的傳播和廣泛被接納,就是發動十字軍東征的肇因[1]。結束戰爭,回到本土,卻發現以神之名發起聖戰的歐洲大陸,卻正在被據說是神怒所帶來的瘟疫所苦,四處瀰漫著死亡。被「信仰」騙去十年青春且幾乎送命的人,回到本土還是無法避開死亡。如果瘟疫是神怒的表現,為何是發生在歐洲,而不是在異教徒的地方呢?這還不算,以前騙了他讓他失去十年生命的那種神棍們,仍然抬著耶穌十架像四處招搖撞騙,隨意誣害女子為女巫,而民眾又集體盲信,因恐懼死亡而胡亂殺人和自殘。如果這就是啟示錄的末日,誰當覺醒?如何覺醒?有沒有條件覺醒?還是,人不過是無意義地出生與死亡,無因無果,一切皆巧合,與灰塵無異,謹此而已?此時此刻,對於神阿爸產生質疑,合理之至。
死亡作為小丑和遊戲
於是,死亡變成了一場又一場與死神的棋局(Game)。騎士為了爭取時間尋找答案,並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可以有好死,便與死神一局一局地下棋/遊戲。這死神也好玩,可能滿有信心自己最後必勝,所以留一個好對手下棋好像也不錯;但祂也會撒賴,矯裝神父騙騎士把對神的懷疑和下棋的步法講出來。「神」在電影中亦有限,竟連撒賴騙取情報之後的一局也未能贏,看得笑出來:柏格曼大叔那時真的很「怕死」啊!
「經由死亡,『我』即化為烏有,穿過黑暗之間。而等著我的,全是我無法控制、預料及安排的東西。這對我來說,有如無底的恐懼深淵。一直等到我突然鼓起勇氣,將死神妝扮成一個白色的小丑,會和人交談、下棋,還沒有秘密,才算是踏出克服自己對死亡恐懼的第一步。」這是柏格曼自己的說法[2]。
「死神作為丑角」這個奇異的處理,除了自我安慰之外,還可能有別的意思嗎?小丑是一種很複雜的概念,也是戲劇中「非常態」的其中一種代表。他必須是可笑的,他必須要嘲笑其他人,或做些自嘲的事情,好像瘋瘋癲癲的,讓大家覺得開心。可是,沒有人是永恆開心的,所以,大家都很容易想像小丑就是「對人歡笑背人愁」的孤獨匱乏型。這種孤獨匱乏型又很容易因慾望過高,而成為對其他人的威脅,故也有一種恐怖感。另一方面,由於小丑的工作便是不斷嘲笑現實,因此,他必須對人們的「現實」保持距離以產生這種幽默感,換句話說,他有另一種視野,故,有時丑角又會有一種「大智若愚」的形象。可能,小丑這個概念之多層次,剛剛好足夠承載導演對「神/真理/死亡」這個如此複雜的命題的情緒和思考。
零點.回到死亡的幾種可能性
雖然柏格曼說他怕死,但是,觀眾可別忘了,恐懼也是人類複雜的慾望之一,否則,哪來如此多人付錢去看驚慄片、去高空跳笨豬跳啊!
死亡,除了如導演自言的「恐懼深淵」以外,也有另外一些意義。
毀滅與創造:片中那名一直沉默的少女,到見到死神才第一次說話,她先是驚恐,最後她跪下,帶著淚水微笑起來:「一切都將完結了。」痛苦終將完結,有什麼不好?啟示錄記載,末日審判後,迎來的是新世界--毀滅與創造,本是一體雙生之物,正如杯不倒空,就不能再盛水一樣。因此,死亡,是既痛苦,又喜悅的事情。
回歸/淨化:死亡,在基督教有句話:「釋勞歸主」--從此解除人生的痛苦勞累,歸於無垠宇宙,回到如母體般安全的狀態,在神的懷抱中,無知、無慾、無苦、無懼。如果說人類因為有「想成為獨特個體」的慾望,而努力把自己與別人分辨開來;那麼,不想孤獨,想「從眾」、想「融合」的慾望,到了終極點,就是死亡,而且,是集體、無差別(亦即平等)的死亡。
如此,可以很容易理解為何某些「極端教派」會相信,集體死亡,一起離開污穢的俗世,是一種「神聖的淨化」。如此,我們也可以明白,為何如影片中像「女巫」這種「散播污染」之人,那些怕死怕得要命的人們對其處決的方式絕不會是斬首或絞刑,而必須是具絕對毀滅性的火刑,還原為塵土才能「淨化」,才能消除「不潔」。影片最後,演員佐夫又見到異象,死神引領著影片中死去的所有人,在遠處山邊的天際線上跳舞。穿越了死亡,死神要求他們手牽手,跳起神聖莊嚴的舞蹈。手牽手的合一意象與騎士告解時自責的冷漠,或者拉菲爾死前孤獨地恐懼,形成鮮明對比。或許,失去與他人連繫的人,只能透過面對死亡的淨化作用,才能進入新生?如此「淨化」這概念又回歸到毀滅(污穢、愚蠢)與創造(潔淨、神聖)的概念之上了。
「末日」這麼勁量級的毀滅,本來就是生之欲與死之欲的最高結合點吧!
物化與儀式:中文叫沒有生命的物件做「死物」。死了,靜止了,沒有人可以再啟動,也沒有人可以再改變這個人的什麼了。在這個人的生命之書上,所有他對自我的理解,都不會有任何新發展。人死變屍,屍即物。人類學經常會研究不同文化中如何克服死亡的儀式,如何事實上安全地進入「物化」或「非常態化」的狀態,而達致一種穿越死亡、克服死亡的安全感,讓人透過這種儀式回到日常生活之中,繼續日常經濟生產[3]。
死神之友
這麼說,整齣電影就是一個物化儀式,就是導演透過將演員和鏡頭「物化」為膠片上的影像,以克服死亡的恐懼?導演是否更透過嘲弄死神,讓死神成為一個小丑,來聊以自慰呢?我想,這個衝動是存在的,不過,如果只有這種程度的自我滿足的話,應該不是柏格曼吧?快感和美感,始終是有分別的。所以我們還要談,死亡的朋友:神聖和遊戲。
死亡在人類整體而言雖是普遍的事,但在每個個體為保持住生存而勞碌的生命中,都只有一次,所以屬於「非常態」,而且是人的計算理性所不能掌握的東西。在「非常態」和「非計算理性」這兩個分類下,當然還有相關的朋友:神聖性和遊戲性。計算的理性是為了「獲取」。死亡是關於「散失」(「塵歸塵,土歸土」)。神聖性要求的,通常是因為信念而祭獻/無條件付出你最好的東西。遊戲則是付出努力而獲得一個愉快的過程--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因為結果本身意味完結,是可以被把握的事實,但不能被「享受」。所以,在遊戲當中若有人「唔輸得」,整個遊戲就會變得「不好玩」啦。這種情況,通常是遊戲被職業化的結果(如職業球賽,根本不是為了「玩」)。
異象.遊於藝
要再談一點遊戲,因為這會直接指向電影內的救贖之途。
朱光潛的美學觀我不完全認同,但關於遊戲的部份我倒是很認同的。在《談美》中他談到,遊戲就是最原始的藝術形態,就如小朋友拿個掃帚扮馬,這有模仿現實的性質,但又不是完全的現實,也有主觀想像的客觀化、形象化和虛擬化。幾個小朋友繼續共同確認那是馬就是馬,就可以繼續玩下去。這簡直是一種「說有光就有了光」的神創嘛,但這是每個小朋友都很容易會學懂去玩的遊戲,而且完全只是為了開心的,不是計較自己「實質」獲得什麼東西。[4]
柏格曼的自述中曾提到他小時候,只要創造了一些什麼東西,就很想引人注意,想獲得確認,以至後來亂編故事跟朋友講,但又因太瞎扯所以經常被「踢爆」而恥笑。最後,這個小朋友就把他的創造力,收藏在他孤獨的世界裡。這種編故事的動作,很明顯也屬於「遊戲」的範疇,可是,由於他是在現實生活中杜撰有關真實的故事,會導致真實/虛構的混淆,這就跌入了現實世界的「謊言」的道德範疇,於是這個小朋友當然會惹到一點麻煩。
有看過《第七封印》的朋友,應該馬上會發現:這個小朋友不就是那個說看到「異象」演員佐夫嗎?
在電影中,具有這種遊於藝的特性的,共有四個:隨從、演員佐夫、教堂畫師、死神。
死神我們談過了,來看看其他三個人類吧。
隨從好像是騎士的世俗一面。當騎士還在信仰與否之間掙扎時,他不見得心情平靜。在他與教堂畫師及神棍拉菲爾的對話中,可見這人腦袋清晰,知道主人和自己都是被那些神言神語騙了,浪費了十年青春,心裡是很憤怒的。他不會想神不神的問題,只會編一些市井巷里的滑稽色情歌來放輕鬆。他心地不壞,見到神棍欺負弱村女會拔刀相助,也曾有衝動要去救那明顯是被「祭旗」的少女。不過,見到美女,他也是期望回報的。他一直在害怕死亡,在教堂見到恐怖的畫會怕,但又不肯認;到最後面對死神時,他發脾氣講了一堆話,最後他說:「我會保持沉默,因抗議之名。」
演員佐夫在電影中似乎是「藝術」的代表。一開始他就見到異象(聖母瑪利亞和聖嬰),並對自己見人之不能見的能力深信不疑,故也對自己(創造)出來的事物深信不疑。無論妻子和旁人如何說他不過是痴人說夢,他還是深信自己的「夢」就是真實,或至少是真實世界的一部份。最後,他和家人的純真、善良和愛,也成為了騎士找到的意義,也就是,值得記憶、捍衛和犧牲的東西。
畫師呢?畫師和隨從簡直一見如故,言談甚歡,大談之聖戰與教會之無聊。教堂畫師負責把末日景象仔細畫出,他的畫畫心得是:要畫得很恐怖,突出恐怖細節,讓信眾害怕,這樣他們才會把自己送給教士們主宰。對於此,他持世故而諷刺的姿態,卻只能維持工作。
同是藝術工作者,畫師雖然心底明了,卻沒有演員佐夫對藝術的執著。佐夫對藝術的態度,可見之於他和劇團老闆最早的對話中。當時他們的三人劇團應教士之聘到某村,演一些嚇人的戲劇,去令村民認罪悔改之類,老闆還在選用什麼可怕的面具,佐夫卻說,不如演些風流韻事,人們喜歡看呢。(結果風流韻事卻成了老闆和鐵匠妻子的「真人騷」了…)這裡佐夫所講的風流韻事,其意義絕不是我們現今講的八卦,而是一些令人開心發笑的事情,一些生活的樂趣,而不是協助那些一心煽動人們的恐懼情緒,以達到自己控制目的教士們,拒絕繼續幫他們為群眾洗腦。
這個演員和現實世界最多衝突。先是與劇團老闆有點口角,不願意演教士付錢要演的戲。然後,明明沒事人在餐廳吃點東西,忽然間不幸遇到那個剛被隨從打過、滿肚火的神棍拉菲爾。這拉菲爾曾欺騙不少虔誠的少年離鄉別井去打「聖戰」,令別人妻離子散,只為證實自己是得神授。後又因無法繼續在神學院騙飯吃,成了在瘟疫村裡專偷死人身上財物的小偷。他充滿無名的妒恨,甚至於發泄在一個無辜的佐夫身上,以最離譜的身份政治(你老婆跟一演員走了,這個也是演員,所以他也該殺!)來煽動鐵匠和群眾,大家一起以羞辱和傷害這個無辜者為樂。這次是隨從救了佐夫,佐夫逃跑時,也不忘偷走神棍偷來的美麗手鐲送給妻子。他的妻子米亞很善良也很愛他,而且也同是演員,可是卻總覺得他在亂編故事。在這次他被欺負後,由於不明就裡,米亞就道出了自己對丈夫一貫的看法:「都叫你不要成天跟人說見到異像」、「都叫你不要又扮傻瓜懶風趣」,因為「會惹人家生氣的!」只是,為何這位女子又深愛一個這樣的做夢者呢?世上有一種愛情是欣羡對方會做一些自己不敢做不會做的事,米亞的愛情,大概就屬於這一類吧。
這演員的一家的生活和態度,最終成為了尋找真理和神的騎士找到那件「有意義」的、可以讓他死得好事情。騎士為爭取時間讓他們逃跑,打翻了棋子,這一局,死神勝了,救了這家人一命之後,騎士以棋局向死神做的延期申請便即將到期了。
影片裡,能夠洞察世情的、遇神跡的、能反抗的、能愛護的、能提出異見的、見義勇為的人類,都是能「遊於藝」的人,而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一點丑角的味道(隨從的滑稽歌曲、演員經常想逗人笑、畫師的自嘲)。他們對世界都有一種幽默感,而幽默感來自什麼呢?就是來自一種對「既定現實」的質疑,一種能從另一種視角看待事物的方式,不盲信,如演員佐夫說:「我看到一種真實,只不過不是你們看到的真實。」透過「遊於藝」,人類也獲得了和死神這個神格角色相似的性質了。
不過,這還是不夠的。因為,柏格曼大叔想做的,是樹立另一個人類可以有的生活概念,去代替教會所帶給人們的「神」的概念。
神阿爸
有一場戲,死神扮神父,騙取下棋情報,這兒除了嘲弄一下死神這,「小丑」外,導演還借助騎士的口來一堆「天問」,如:「為什麼他總是藏在半真半假的承諾和從未實現過的奇蹟背后呢?」「當我們缺乏信念的時候,又如何信呢?」「難道要相信那些我們不想也不能相信的事情嗎?」「為何我不能殺死心中的上帝?」「為何他使我蒙羞?」「為何他總像一個我無法擺脫的嘲笑者?」
最後不再是問題:「我需要真理,不是信仰,不是承諾,而是真理。我希望上帝能伸出他的手,露出他的臉,和我說話……或許那里根本沒有任何人……那麼生命真是荒誕而可怕。沒有人可以活著面對死神……」
於是柏格曼弒父了,他宣稱,人們口中的上帝,不過就是一個為克服怕死而生產出來的慾望對象,換言之,所有的崇拜及其相關之物,只是人為怕死而做的物化儀式。這實在是心理上的弒父行為,除了殺掉神阿爸這個想像,也是對身為牧師的父親的反叛。雖然這弒父到最後是有「補鑊」的,到騎士真正面對死亡時,他還是恐懼地向神禱告了。
作為牧師的兒子,他當然應該知道基督教其中一種重要的智慧:不准拜偶像。本來,這是要求信眾自發為信念而愛人和謙卑,而不以計算理性的「獲取」為最高生活綱領。不過,神阿爸有神阿爸講,子女通常都不聽啦。正因為神和死人一樣都不會發話,於是,更容易被物化,亦即是隨大家慾望是什麼就什麼吧。越有權力的人,就越容易傳播這種偽神論,整齣電影的聖戰背景,就是這種事情。「他人即地獄」這個詛咒,是連神也不能倖免的悲劇。柏格曼是否真的解決了神阿爸,那是他內心的事,我實不敢說。不過,他肯定解決了教會。影片裡,每逢教士出現都沒有好事,所有人都墮入一種為了克服死亡恐懼而不斷自殘及互殘的狀態。這不是啟示錄所談的偽神的廣泛傳播和接納是什麼?
如果「神」只是人們腦海裡的概念,心靈中的慾念,那麼,要討論的重點,就不是「神存在與否?」,也不是「點樣得好死?」,而是:「即使我們真的只是如灰塵般無因無果的偶然存在物,我們仍可有什麼活下去的意義?」「我們憑什麼活下去?」「要活下去的話我們要守護什麼?捍衛什麼?」
愛.遊於藝
藝術,就是創造,是基於現實之上的另一些真實,是現實的無限可能性(異象),就如小朋友説掃帚是馬就是馬,神說有光就有了光,是人類最大的自由。透過這種自由創造的能力,人可以在宇宙之間遊走,用中式的說法就是物我兩忘、逍遙遊,用西方的說法就是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充滿過程,有事「發」、「生」,才有生命力。雖然與死亡一樣,都是從個體生命回歸宇宙穹蒼,但這與死之慾的「安頓」、「安息」於宇宙之中,成為「物」的一部份的狀態不同。
可是,諸君請勿誤會,我不是說自稱藝術家的人就擁有那些能力,因為這是柏格曼用來代替作為偶像而存在的「神」的概念,所以絕不會是特定的人,而是一種概念,這概念需要存在於每個人心目中,但,胡思亂想也要也會有個方向,引發這個概念運作的動能在哪裡呢?
是基於對生命/創造的愛,而不是基於對死/損失的恐懼。
在電影中,演員佐夫一家的蓬車停在一處休息,剛好騎士也停在那裡,可以說是一種萍水相逢的狀態。當時佐夫不在,米亞則在照顧孩子,騎士便與她聊起天來。不久,演員回家,隨從和沉默少女也回到騎士身邊。演員佐夫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為大家彈奏一曲自己的作品。本來米亞怕陌生朋友覺得丈夫無聊想阻止他,豈知隨從也有創作歌曲的興趣,於是佐夫就彈起魯特琴來了。
米亞與騎士的談話,出現整齣電影都沒有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有人聆聽他、憐愛他、企圖了解他。騎士自十年戰亂歸來,見到的仍是哀鴻遍野,所見之人際關係,不是恐懼就是操控,再不然就只有隨從與畫師那種冷嘲熱諷,連他自己也認為已迷失在對其他人的冷漠之中。只有當遇到佐夫和米亞,他才能見到這種善良、這種平和、這種笑容。這兩夫婦,對一些陌生人,獻出了自己僅有中的最好的給他們:音樂創作、關懷、牛奶和野草莓,而且,在瘟疫流行期間,他們還同用一碗喝牛奶。
這讓騎士發現了,他必須捍衛的東西。
救贖方案?
對陌生人有愛,聆聽陌生人的痛苦安慰他們,對陌生人無條件付出最好的東西,這是很重要的價值。相對於末日的平等性、無差別性毀滅;在這對演員的心中,存有對陌生人的、平等性、無差別性的愛。
其實,無論基督教的普世愛,還是世俗社會所談的公義,都要依靠大家對不認識的人存有這種無差別的愛,同意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生命,才有可能。通過藝術創造而可以遊於宇宙之間,通過保持幽默感和創造力來以另一個視覺看見現實,雖是可貴,但創造原動力必須來自這種普世愛。所以,相比起演員,隨從就無法得救了,他的幽默感和創造力,都源於對死亡的恐懼;而他的見義勇為,也不是無條件的。
這為什麼如此重要?反過來看就知道了:缺乏對陌生人的愛,加上對死亡的恐懼,那些神棍才可以輕易煽動仇恨,讓大家群起來欺負佐夫;也可以隨意把瘟疫的責任推到一個弱小女子的身上,誣蔑她為女巫,而這個動作,就靠大家對陌生人的冷漠、無視才可以做得到。再進一步說,可能那些教士也自以為見到神也說不定。更誇張而悲慘的,是被誣為女巫的少女,被瘋狂轟炸、虐待、洗腦後,連自己也以為自己真的是撒旦附身的魔女。這些也是「另類視角」,但由於這些都不是根植於對生命的愛,所以,便一塌糊塗,累人累己。
其後……
根據編輯的要求,是要談這個「末日出路」的問題。
以我見過文本之中,末日方程式不外乎三大類:接受、不接受和話之你。
話之你,今天有酒今天醉,做壞了這個世界令下一代要在廢墟中生活唔關我事。其他人提到末日就擔心一下,然後轉個頭又沉淪於消費當中。這類人應該是最多和最「正常」的。
舊約聖經裡的諾亞方舟、出埃及記、巴別塔等集體被神殺的故事,或極端教派集體自殺自救,或者教眾進行恐怖襲擊以推快末日/新世界的來臨,這些都明顯是接受末日/新世界的例子。
至於不接受的故事,就與「自決」和「救贖」有關,這就主要訴諸兩種方向:一是個人學懂愛他人的修為(通常都是宗教、靈修、心靈雞湯之類);二是自我組織、連結起來反抗俗世建立出來的偽真理,亦即現在正把我們帶向地球荒廢的那個體制。
這兩種方式我私以為缺一不可。革命也好運動也好,如缺乏對陌生人的愛,只懂以死之慾的眼光不斷看結果、不斷保護已「獲取」的,而絕不看過程中生發的素質,這樣可以帶來很可怕的後果。可是,缺乏對體制和個人在體制中的位置的深切反省,被欺壓的無權勢者不群起而反抗的話,如此就想妄談改變,無異於自欺欺人:人不組織起來成為足夠反抗體制的力量,就只有等到地震海嘯等大災難真的發生,引爆了核電,才會有足夠的牙力叫停核能。
柏格曼的想法,應該較傾向於個人修身的部份吧,否則,相信整個寓言體系中,會出現較多不同層級的教士們的對話,或出現較多那些貧苦大眾面對死亡的不同想法,或是教士與信眾之間的經濟關係(中世紀的贖罪卷買賣就很有現代商品的象徵意味)……
這種修身的傾向,令到《第七封印》的救贖方案裡,在具體的「個人」和抽象的「人類」當中,似乎沒有「社群」這個概念。一位注重獨立思考的重要性的藝術家,觀察到人在群體之中可能產生的盲目,是值得我們留意的。社群乃是孕育個體成為「人」的安全網,可以是共同體的建立,可以是無權勢者抵抗不公義的可能;但也可以是排斥異類、欠缺包容的單細胞性集體。在這個時候,個體的價值,與抽象普遍無差別的「人」的價值,就是平衡的基準。
可是,在電影裡,「社群」的出現,全都只是集體的盲信和胡來,人在社群中好像誓必失去獨立判斷。於是,能得救的只有長期不在社群當中的遊牧藝人,能在死亡邊緣暫時自救救人的也只有作為特權階級、知識份子的騎士和他那有一點墨水的隨從。被欺壓、被欺騙的人群,只有被虐待或者被救助的份,且最終還是免不了死亡。在談末日、自決、救贖的主題時,完全不處理小社群,單談精神自我救贖法,對於人類整體的將來,是否可行,實在大有商榷。就像全無社群關係的遊牧藝人佐夫,在面對人群和偽真理的欺凌時,是很無助的,只能被人打救,可是,在與騎士及隨從分別後,他又如何呢?再延伸一點去想,佐夫常說自己看到神的異象,這終有一天會激怒那些以神為專業的教士,到時他妻子會不會被誣為女巫,蠱惑丈夫?在當時的社會而言乃大有可能,到時,誰可以救他們?
一齣電影未必可以處理所有相關於末日這個大命題的東西。不過,了解一個作品或一個人,都可以同時從他有和他沒有的、他是與不是的地方入手。最後,可能形成一種叫「批評」的東西,但這個「批評」到底是出於渴望了解的愛人之情,還是出於渴望「獲取」優越感,乃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吧。
不過,如果採用過度/延展閱讀的方式,也可以這樣說:怕死的人需要極多物化的儀式,以克服死亡的恐懼感,因此需要極多計算理性,去把自己的所得不斷累積。在啟蒙時代之後,在一個「神已死」的世界中,商品拜物教就成了取代神像而存在的,用以克服死亡的偶像。商業社會靠什麼來做到貨如輪轉?當然就要靠有系統和大量地生產、刺激恐懼感和匱乏感。然而,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當人們怕死的感覺越來越失控,地球被耗盡的一天,大家都不得好死的一天,也會更快到臨吧。
可是,要思考怎樣做,可能要先面對死神的這句甚有佛家意味的話:i am unknowing.
因為,末日到臨時,沒有人是無辜的。
筆者按:
由於不懂瑞典語,一切對對白的理解,只源於英文字幕。